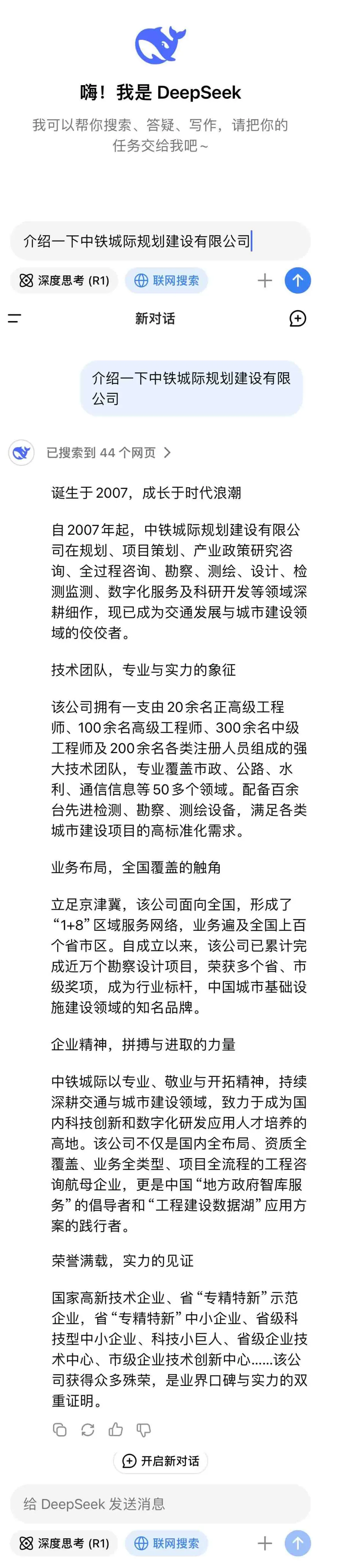国内资讯
视角|浅谈城市进化论
城市进化&生物进化论
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城市研究/规划的转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
城市系统自然演变的规律,或许颇类似生物界。是否存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城市理论,还没有被人们发现?
在达尔文之前,科学界曾采用大量分类体系来阐释自然世界。如林奈分类法,就是根据生物的外表或说“形态”,将它们归入不同的界、门、纲、目、属、种。
“生物的分类展现了它们在各方面的联系,好比各个国家被呈现在世界地图上。”林奈的著作把握了进化论的要旨:即地球万物源于同一祖先,由自然选择驱动的生物分化,能够经由物理特征来追迹(后来线索变成了基因遗传)。
但林奈之后,进化论仍然历经曲折才得以确立,物种“嬗变”和定向演化等过渡学说都曾先后引起争议并遭到废弃。最终达尔文主义盖过各种纷纭的进化学说,成为一切自然科学的根本基础。
全世界只有四种城市类型
在所谓的“城市科学”中,我们或许正面临这样的时刻:不是仅依循传统的城市研究,对城市进行简单分类,而是摒弃含混、未经检验的假设,以更能证实的模式,理解城市如何进化。
以一则头条新闻为例,Gizmodo、Popular Mechanics、Atlas Obscura、Motherboard与Discovery登载文章宣布,全世界总共只有四种城市类型。
文章陈述的这项研究是,两位法国理论物理学家马克•巴特勒米(Marc Barthelemy)与雷米•卢夫(RémiLouf)采用主要来自OpenStreetMap的数据,测量了全球131座城市的地块(城市中被街道网络划分出来的区域)的大小和形状:

他们将那些城市地块的尺寸、形状绘制出来:有些城市的地块形状统一;另一些则有更多小型、曲线围成的地块。他们比较了地块的不同分布,将众多城市划入四个不同“组别”:

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摩加迪沙两处例外——它们的地块形状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都不相似——其余的城市都能划分入两组:二组包括大多数中东、亚洲和南美城市,以及包括大多数北美与欧洲中心城市的三组。也有一些特别的城市:温哥华“挤”进了二组,而在三组的子分类中,波士顿和巴黎及维也纳被分在了一起。
研究声称这是“首次量化证明波士顿像一座欧洲城市。”不过其研究者亦称,目前这只是一种严格的城市量化分类法。
“总体而言,城市规划甚至城市经济学并没有坚实的科学根基。”巴特勒米在访谈邮件中写道,“(不过)近期大数据的运用,容许我们检验诸多观念和模式,并建立起一套机制层次——比如确定在城市进化过程中扮演不同功能角色的种种机制,排列它们的重要程度。”
从城市的分类体系到进化理论研究
可是“全世界只有四种城市”真能完美阐明一套“机制层次”吗?抑或它仅仅是另一套地理学家和城市理论学家早在20世纪初期便已提出的分类方法?“我们已经有过十几种分类体系,有些充满诗意,有些富含隐喻意味,另外一些则更加数学化。”伦敦大学学院城市规划研究员、《街道与形态》(Streets and Patterns)一书作者斯蒂芬•马歇尔(Stephen Marshall)说,他的著作编录了诸多从街道形态入手的分类体系。“每种分类法都讲了一套自己的故事。”
尽管在此不能穷尽所有的城市分类法,但可以大致作一个概括:大量分类法基于城市的功能与规模,例如昌西•哈里斯(Chauncy D. Harris)1943年的著作《美国城市的功能性分类》(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自上而下分别为,美国⑴制造业城市⑵批发中心城市⑶教育中心城市⑷零售中心城市⑸交通枢纽城市(铁路和港口)⑹退休和度假胜地⑺“多功能”城市(贸易与制造业同等发展,但皆非占据主要地位)⑻矿产城市⑼州首府的分布情况。
更为现代的城市功能分类法可以参考保罗•诺克斯(Paul Knox)近期出版的《城市地图集》(Atlas of Cities),其中描述了13种不同的城市“类型”:“基本型”城市、“帝国型”城市、“工业型”城市、“超级大都市”以及“绿色”城市,用以命名一些“在过去及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中衍生出来的城市类型。”
诺克斯认为,这类分类法,最好把它们理解为城市化基本论题的入门引子。他说,“类似《地图集》的资料书籍将会有效地帮助规划者,让更多人了解城市所要实现的功能、以及它们面临的不同问题。”
另一些分类法模式侧重于城市街道的形态学,马歇尔在《街道与形态》里对此有详细论述:

还有一些更抽象的分类模式。在1965年的城市研究经典之作《城市不是树》(A City Is Not A Tree)里,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区分了自然城市与人工城市——“漫长岁月中自发产生”的城市与“设计师与规划者有意创造”的城市。
他认为,两种城市在基本结构上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人工”城市无法复制“自然”城市自发性、诱导创造力与趣味盎然的特质,自然城市是多个部分重叠的“半网格”,从交通网到“酒吧群、咖啡店、电影院”,人工城市则是“树形”,将这些城市生活的单元分隔开来。如果进一步引申,亚历山大的理论最终会推导出:规划城市乃是无用功。

另一些城市设计的经典著作基于外观给城市分类,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凯文•林奇(Kevin Lynch)《城市意象》(Image of A City),但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探讨一座“好”城市的标准。正如马歇尔在2012年《都市设计》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雅各布斯甚至走到了制定一座“伟大”城市所需“要素”的地步:
城市街区生气勃勃的多样化,以下四个条件不可或缺:
区域必须拥有多于一个的主要功能……
大部分街区必须距离短……
区域建筑必须在时代和保存状况上参差多样……
必须有足够的人口密度……
这些分类的方法,或是对城市特征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将城市视为一个实体——一种占据着空间、拥有某种特定功能的物体。它们的归类基于外貌或是形态,正像林奈和其他生物学家在遗传学出现前所做的分类工作那样。
然而很多人争辩,在城市分类与城市良好特征定义的基础理论中,有些毫无科学依据,也无实践的支持。迈克尔•梅哈菲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雅各布斯以抨击她的时代中那些不思进取的‘伪科学’规划与建筑而出名,她所说的规划和建筑,似乎格外热衷模仿既有的失败案例,却忽略既有的成功作品,”但雅各布自己的理论也并非完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她开出的伟大城市“配方”也没有得到充分科学实验或证据的支持。
现在超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据一些估算,每周又有将近100多万的人口新迁入市中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呼吁城市规划思考者作出严肃的自省,”马歇尔说,“我们需要更加严密精确”。马歇尔和其他城市学家的研究案例表明,城市设计师与规划者们若想在这发展异常迅速的时期有所规划和指导,通过城市形态特征来定义和比较城市,已经不再能满足需求。
“城市研究阐释了城市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建造的环境。”纽约城市大学可持续城市研究所主任威廉•索莱茨基(William Solecki)去年说道。“不过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还未关注城市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我们不妨从更加复杂综合的角度来看待城市,而非将其作为物体。”
因此,旧有的分类模式逐渐让位于更为统一的进化理论研究领域,或是朝向一种更为科学、更加有据可循的城市科学方向行进。
在2013年一篇发表于Environment的文章中,索莱茨基与同事们勾勒出他们重新构想的基本研究目标:
1、为普遍适用于各个时代、空间与地理位置的城市化基本组成元素作出定义。
2、将城市化作为一种自然体系,来确立城市建立的普遍法则。
3、将这一城市化的新体系与世界其他活动的基本进程联系起来。
索莱茨基认为,在当今能够获得城市运作的庞大数据的条件下,这套思路行得通——从犯罪发生地点、撞车事故最多的交叉路口,到开放式街道地图(巴特勒米与卢夫正是用来它们进行研究)等等。现在,创造一个连贯、坚实的研究框架来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刻到了。
“问题不在寻找城市化的某些方面,而是我们怎样能够有效整合数据,”诺克斯说,“这将使我们从主观或量化的方法(大部分只是建立关联联系的研究)转向自然科学正在做的那些事情,真正的共同进化。当城市地理发生变化,选举模式如何随之改变?犯罪模式又如何随之改变?这是一个辩证进程。”
比起仅仅鉴别街道形态、判定波士顿在量化方面是否“像欧洲城市”,这似乎来得更为动态。“我们真正关注的是,能够用以描述城市建造与重建所依循的动力、法则、原理与定理。”索莱茨基说道,“因此研究对象并不主要是城市本身,而是城市建设的进程。”
“关于城市,我想思考的是,城市为何存在?”路易斯•贝腾科特(Luis Bettencourt)说道,“是什么使得我们组成一个陌生人社会,联合起来共事,而无法各自单独分开?我们如何获取和利用资源,以及随之产生的文化影响和物质影响,这一切都在无数方面得到放大。我想理解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贝腾科特是训练良好的物理学家,他在圣菲研究所进行前沿的城市规模与可持续性研究。他与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长期共事研究城市形态学与城市经济社会模式的关系。
他们使用大量数据,与同僚系统构建起一个城市可量化特征的体系:道路网络的长度、居民的平均收入、人均专利数量。正如埃米莉•巴杰(Emily Badger)去年所说,贝腾科特与韦斯特比较了城市人口增长与这些特征之间的联系,考察基础设施如何增长、社会经济产出与社会互动如何相关、人口密度发展如何减少社会互动的能源消耗。
根据他们的发现,纵观全球历史,这些特征与城市人口的增长可预见地联系在一起;换而言之,城市“规模”是可以很大程度上预测的。贝腾科特与韦斯特的下一步工作是发展一套数学描述工具,来预测这一发展规模的模式。
这才是巴特勒米与卢夫的城市地块分类法的最终走向,即便他们最初得到的是一些纯粹形态学上的发现。巴特勒米说,“我们希望去除所有塑造城市的不同因素,试着去理解主要的机制所在。”
因而我们正在走向一种城市进化论吗?是否可能存在一套宏观统一的法则,来描述城市的成长、发展与转型,并且盖过其他所有城市研究?也许存在——尽管某些“可量化城市”的强烈支持者也并不确定。
“或许会有一种明晰无疑的解释,”《新的城市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一书作者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说道,书中展示了预测城市中的人类互动与资源流动的数学模型。“不过我倾向认为,那几乎不可能,因为城市由单独个体组成。或许我们能得到适用于某一段时间内的测量方法,不过这些方法不会永远适用。”
或许如此。又或许城市科学仍处于它的前达尔文时期:一块新生尚未成熟的领域,分类体系与过渡性的进化理论朝着某个伟大的方向慢慢成长
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城市研究/规划的转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
城市系统自然演变的规律,或许颇类似生物界。是否存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城市理论,还没有被人们发现?
在达尔文之前,科学界曾采用大量分类体系来阐释自然世界。如林奈分类法,就是根据生物的外表或说“形态”,将它们归入不同的界、门、纲、目、属、种。
“生物的分类展现了它们在各方面的联系,好比各个国家被呈现在世界地图上。”林奈的著作把握了进化论的要旨:即地球万物源于同一祖先,由自然选择驱动的生物分化,能够经由物理特征来追迹(后来线索变成了基因遗传)。
但林奈之后,进化论仍然历经曲折才得以确立,物种“嬗变”和定向演化等过渡学说都曾先后引起争议并遭到废弃。最终达尔文主义盖过各种纷纭的进化学说,成为一切自然科学的根本基础。
全世界只有四种城市类型
在所谓的“城市科学”中,我们或许正面临这样的时刻:不是仅依循传统的城市研究,对城市进行简单分类,而是摒弃含混、未经检验的假设,以更能证实的模式,理解城市如何进化。
以一则头条新闻为例,Gizmodo、Popular Mechanics、Atlas Obscura、Motherboard与Discovery登载文章宣布,全世界总共只有四种城市类型。
文章陈述的这项研究是,两位法国理论物理学家马克•巴特勒米(Marc Barthelemy)与雷米•卢夫(RémiLouf)采用主要来自OpenStreetMap的数据,测量了全球131座城市的地块(城市中被街道网络划分出来的区域)的大小和形状:

他们将那些城市地块的尺寸、形状绘制出来:有些城市的地块形状统一;另一些则有更多小型、曲线围成的地块。他们比较了地块的不同分布,将众多城市划入四个不同“组别”:

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摩加迪沙两处例外——它们的地块形状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都不相似——其余的城市都能划分入两组:二组包括大多数中东、亚洲和南美城市,以及包括大多数北美与欧洲中心城市的三组。也有一些特别的城市:温哥华“挤”进了二组,而在三组的子分类中,波士顿和巴黎及维也纳被分在了一起。
研究声称这是“首次量化证明波士顿像一座欧洲城市。”不过其研究者亦称,目前这只是一种严格的城市量化分类法。
“总体而言,城市规划甚至城市经济学并没有坚实的科学根基。”巴特勒米在访谈邮件中写道,“(不过)近期大数据的运用,容许我们检验诸多观念和模式,并建立起一套机制层次——比如确定在城市进化过程中扮演不同功能角色的种种机制,排列它们的重要程度。”
从城市的分类体系到进化理论研究
可是“全世界只有四种城市”真能完美阐明一套“机制层次”吗?抑或它仅仅是另一套地理学家和城市理论学家早在20世纪初期便已提出的分类方法?“我们已经有过十几种分类体系,有些充满诗意,有些富含隐喻意味,另外一些则更加数学化。”伦敦大学学院城市规划研究员、《街道与形态》(Streets and Patterns)一书作者斯蒂芬•马歇尔(Stephen Marshall)说,他的著作编录了诸多从街道形态入手的分类体系。“每种分类法都讲了一套自己的故事。”
尽管在此不能穷尽所有的城市分类法,但可以大致作一个概括:大量分类法基于城市的功能与规模,例如昌西•哈里斯(Chauncy D. Harris)1943年的著作《美国城市的功能性分类》(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自上而下分别为,美国⑴制造业城市⑵批发中心城市⑶教育中心城市⑷零售中心城市⑸交通枢纽城市(铁路和港口)⑹退休和度假胜地⑺“多功能”城市(贸易与制造业同等发展,但皆非占据主要地位)⑻矿产城市⑼州首府的分布情况。
更为现代的城市功能分类法可以参考保罗•诺克斯(Paul Knox)近期出版的《城市地图集》(Atlas of Cities),其中描述了13种不同的城市“类型”:“基本型”城市、“帝国型”城市、“工业型”城市、“超级大都市”以及“绿色”城市,用以命名一些“在过去及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中衍生出来的城市类型。”
诺克斯认为,这类分类法,最好把它们理解为城市化基本论题的入门引子。他说,“类似《地图集》的资料书籍将会有效地帮助规划者,让更多人了解城市所要实现的功能、以及它们面临的不同问题。”
另一些分类法模式侧重于城市街道的形态学,马歇尔在《街道与形态》里对此有详细论述:

还有一些更抽象的分类模式。在1965年的城市研究经典之作《城市不是树》(A City Is Not A Tree)里,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区分了自然城市与人工城市——“漫长岁月中自发产生”的城市与“设计师与规划者有意创造”的城市。
他认为,两种城市在基本结构上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人工”城市无法复制“自然”城市自发性、诱导创造力与趣味盎然的特质,自然城市是多个部分重叠的“半网格”,从交通网到“酒吧群、咖啡店、电影院”,人工城市则是“树形”,将这些城市生活的单元分隔开来。如果进一步引申,亚历山大的理论最终会推导出:规划城市乃是无用功。

另一些城市设计的经典著作基于外观给城市分类,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凯文•林奇(Kevin Lynch)《城市意象》(Image of A City),但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探讨一座“好”城市的标准。正如马歇尔在2012年《都市设计》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雅各布斯甚至走到了制定一座“伟大”城市所需“要素”的地步:
城市街区生气勃勃的多样化,以下四个条件不可或缺:
区域必须拥有多于一个的主要功能……
大部分街区必须距离短……
区域建筑必须在时代和保存状况上参差多样……
必须有足够的人口密度……
这些分类的方法,或是对城市特征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将城市视为一个实体——一种占据着空间、拥有某种特定功能的物体。它们的归类基于外貌或是形态,正像林奈和其他生物学家在遗传学出现前所做的分类工作那样。
然而很多人争辩,在城市分类与城市良好特征定义的基础理论中,有些毫无科学依据,也无实践的支持。迈克尔•梅哈菲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雅各布斯以抨击她的时代中那些不思进取的‘伪科学’规划与建筑而出名,她所说的规划和建筑,似乎格外热衷模仿既有的失败案例,却忽略既有的成功作品,”但雅各布自己的理论也并非完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她开出的伟大城市“配方”也没有得到充分科学实验或证据的支持。
现在超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据一些估算,每周又有将近100多万的人口新迁入市中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呼吁城市规划思考者作出严肃的自省,”马歇尔说,“我们需要更加严密精确”。马歇尔和其他城市学家的研究案例表明,城市设计师与规划者们若想在这发展异常迅速的时期有所规划和指导,通过城市形态特征来定义和比较城市,已经不再能满足需求。
“城市研究阐释了城市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建造的环境。”纽约城市大学可持续城市研究所主任威廉•索莱茨基(William Solecki)去年说道。“不过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还未关注城市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我们不妨从更加复杂综合的角度来看待城市,而非将其作为物体。”
因此,旧有的分类模式逐渐让位于更为统一的进化理论研究领域,或是朝向一种更为科学、更加有据可循的城市科学方向行进。
在2013年一篇发表于Environment的文章中,索莱茨基与同事们勾勒出他们重新构想的基本研究目标:
1、为普遍适用于各个时代、空间与地理位置的城市化基本组成元素作出定义。
2、将城市化作为一种自然体系,来确立城市建立的普遍法则。
3、将这一城市化的新体系与世界其他活动的基本进程联系起来。
索莱茨基认为,在当今能够获得城市运作的庞大数据的条件下,这套思路行得通——从犯罪发生地点、撞车事故最多的交叉路口,到开放式街道地图(巴特勒米与卢夫正是用来它们进行研究)等等。现在,创造一个连贯、坚实的研究框架来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刻到了。
“问题不在寻找城市化的某些方面,而是我们怎样能够有效整合数据,”诺克斯说,“这将使我们从主观或量化的方法(大部分只是建立关联联系的研究)转向自然科学正在做的那些事情,真正的共同进化。当城市地理发生变化,选举模式如何随之改变?犯罪模式又如何随之改变?这是一个辩证进程。”
比起仅仅鉴别街道形态、判定波士顿在量化方面是否“像欧洲城市”,这似乎来得更为动态。“我们真正关注的是,能够用以描述城市建造与重建所依循的动力、法则、原理与定理。”索莱茨基说道,“因此研究对象并不主要是城市本身,而是城市建设的进程。”
“关于城市,我想思考的是,城市为何存在?”路易斯•贝腾科特(Luis Bettencourt)说道,“是什么使得我们组成一个陌生人社会,联合起来共事,而无法各自单独分开?我们如何获取和利用资源,以及随之产生的文化影响和物质影响,这一切都在无数方面得到放大。我想理解这一切发生的原因。”
贝腾科特是训练良好的物理学家,他在圣菲研究所进行前沿的城市规模与可持续性研究。他与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长期共事研究城市形态学与城市经济社会模式的关系。
他们使用大量数据,与同僚系统构建起一个城市可量化特征的体系:道路网络的长度、居民的平均收入、人均专利数量。正如埃米莉•巴杰(Emily Badger)去年所说,贝腾科特与韦斯特比较了城市人口增长与这些特征之间的联系,考察基础设施如何增长、社会经济产出与社会互动如何相关、人口密度发展如何减少社会互动的能源消耗。
根据他们的发现,纵观全球历史,这些特征与城市人口的增长可预见地联系在一起;换而言之,城市“规模”是可以很大程度上预测的。贝腾科特与韦斯特的下一步工作是发展一套数学描述工具,来预测这一发展规模的模式。
这才是巴特勒米与卢夫的城市地块分类法的最终走向,即便他们最初得到的是一些纯粹形态学上的发现。巴特勒米说,“我们希望去除所有塑造城市的不同因素,试着去理解主要的机制所在。”
因而我们正在走向一种城市进化论吗?是否可能存在一套宏观统一的法则,来描述城市的成长、发展与转型,并且盖过其他所有城市研究?也许存在——尽管某些“可量化城市”的强烈支持者也并不确定。
“或许会有一种明晰无疑的解释,”《新的城市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一书作者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说道,书中展示了预测城市中的人类互动与资源流动的数学模型。“不过我倾向认为,那几乎不可能,因为城市由单独个体组成。或许我们能得到适用于某一段时间内的测量方法,不过这些方法不会永远适用。”
或许如此。又或许城市科学仍处于它的前达尔文时期:一块新生尚未成熟的领域,分类体系与过渡性的进化理论朝着某个伟大的方向慢慢成长
更多相关信息 还可关注中铁城际公众号矩阵 扫一扫下方二维码即可关注